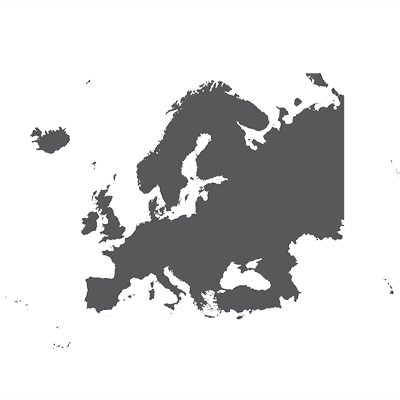我们在山中营地搭篷睡下,凉凉夏夜,帐篷后的竹丛不时发出响动,未曾熟睡的我,整夜听闻牛低低地哞叫,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清晨起了大雾,那连绵朦胧的山,绿的光影忽隐忽现,赤道孩子穿越山海寻夏,不知夏全在山海,以为自己醒在了云朵之上。
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
bluebirds fly
夏末,蝉叫声此起彼落。隔着一面窗,那棵矮矮的树,风吹,它就动,风止,它就静成一幅画。总有甜浓的馨香不时飘进房里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最后一季松红梅。
至纽西兰前,我怀疑过,这南方以南的香格里拉、上帝的后花园,是否因为这年代太多人的描述,而显得 “旧” 了,“老” 了。
甚至关于夏的概念本身就带着狂热与难耐,我从不曾想它。
以至于抵达纽西兰翌日,情人节,当我杵立在海岸对街的水果雪糕店,咬下第一口雪糕时,我的脑竟空空的,只感到某种柔顺、无邪的滋味。原来简单的快乐说的是这种。我手握甜筒,和 Kite 经过一对坐在沙滩椅上看海的老人,走上芒格努伊山(Mount Maunganui)。海面金光闪闪,几只小羊在斜坡上吃草,青青的草,荡漾着,一朵朵细小的花像天上的星星,在剑光之下闪动。
鸟儿四处觅食,但它没有啄我手上的雪糕。
雪糕一点一点,与我的身一起融化了。



工作的周末休日,Kite 的摩多车后边坐着我,疯狂的阳光,地上的人,绕过一个海湾,转头又是一个海湾。累了,我躲在阴影处,看晴朗的天,蓝得不能再蓝的海,独立待在悬崖边的树……我们在山中营地搭篷睡下,凉凉夏夜,帐篷后的竹丛不时发出响动,未曾熟睡的我,整夜听闻牛低低地哞叫,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清晨起了大雾,那连绵朦胧的山,绿的光影忽隐忽现,赤道孩子穿越山海寻夏,不知夏全在山海,以为自己醒在了云朵之上。
再吃水果雪糕,在陶波(Taupo)。陶波巨大的湖没有妖怪,湖上有山峰。市中央有辆雪糕车,卖雪糕的老奶奶说,酸甜浆果准没错,便跟她要一支 boysenberry。雪糕新鲜做好,淡淡的紫色,温柔、迷人,一吃,似水还非水,盛夏里,奶与蜜交织的梦从心底流出。
在陶波,身旁的朋友是 P。 P 七年前到纽西兰,现如今和当地男友种田养牛过日子。我们走进一家家手信店里闲晃,谈论着给家乡的谁送什么礼物。午后,我们喝咖啡,说旧事,最后来到雪糕车跟老奶奶买雪糕。 P 说话时乡音依旧,谈话间老用手拂弄头发,恐怕头发有一丝紊乱,和小时候一样。




有一个故事。离纽西兰半个地球以外的热带岛屿国度,小女孩跟着母亲出发远地工作,临行前母亲在杂货店买了一支草莓雪糕。小女孩好高兴啊!她撕开包装纸,大口吃起来。一滴融化的雪糕滴到了小女孩洁白、美丽的裙上。母亲勃然大怒,要知道,她给女儿的快乐都是用自己的幸福换来的!于是一路咒骂添麻烦的女儿。小女孩抽泣着,边哭边吃完雪糕。那天之后,一直到小女孩长大成为女人,她不再吃雪糕。
这伤心的雪糕故事感染了我。吃雪糕时,我偶尔想起那对母女,一个有泪不能流;一个把自己的眼泪吞了下去。
最后一次在纽西兰吃水果雪糕,夏已经走远了。我们在南岛皇后镇(Queenstown),听一头脏辫的旅人路边弹残旧的木琴。早秋的天高而远,一曲完了,手上空空的,哪里还有什么雪糕?一阵风不知从哪儿吹来,片片秋红的落叶撒落满地。
很久以前,当毛利族人的祖先乘坐独木舟,循着夜空中星辰的指引,翻越凶险大海,登上这绿的一片大地时,他们终于寻回曾经失落的故乡。 “Aotearoa” —— 他们如此称呼,长白云之乡,神应许的地方。
飞机上,我给 Kite 讲母女的故事。下回再来,我想带她吃一次莓果与香草,听图伊鸟(Tui)歌唱,趁雾散之时,摊开身上的裙,站到夏日魔幻的光影之中。那时,她会看见远古的毛利人看见的希望。
因为在那里,我们一无所有。